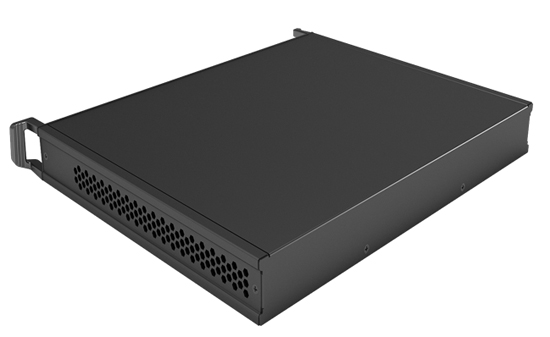留在記憶深處的溫暖
http://www.progcable.com2025年08月25日 09:28教育裝備網
很多年過去了,我還一直記得2007年初秋那個燠熱無比的下午。一場來勢洶洶的驟雨,洗得天空潔凈異常,沒有粉塵的遮擋,炙熱的陽光如同蚊蟲一般,在我脖子上、手臂上和裸露的肩膀上,叮咬出一層細密的紅痱子,額頭上,汗水如同山洪泛濫一般肆虐橫流,接著便好似涂滿全身的漿糊,使我的腳步漸漸變得艱難和沉重起來。
我扛著重重一捆新書,那是我在兩個月前剛出版的長篇小說《云橫點蒼劍氣寒》,這也是我人生的第一本書。在大理古城的亞星飯店門口下了從洱源老家駛向州城下關的班車,我把書往背上一掄,便邁開大步沿著寬闊的水泥路往蒼山方向走去。我的目的地很明確,那便是大約兩公里以外的大理財校。七年前,我還是那里的一名中專生,三年求學生涯,那里有我最純真的青春年華,還有我最親密的同學、最尊敬的師長。
然而我此行的目的卻并不光彩。母校培養了我,我沒給母校作過任何貢獻,但此時我卻是來向母校賣書的。是的,不是送,而是賣。堅硬的水泥坡路似乎沒有盡頭,在烈日下還反射出耀眼的白光,沉沉60多本書壓在肩上,讓人只覺得一陣頭昏目眩,一種難言的羞恥感,如同海邊的浪花連綿不斷襲來,讓我直想丟下書便轉身逃離而去。
但很快,意識戰勝了沖動。那書是我數年筆耕的成果,凝結著我無盡的心血。我們學校位于蒼山腳下,這是剛建成不久的新校區,在那時差不多就是真正的曠野荒郊,想打車是不可能的。我只能把書從左肩換到右肩,在樹蔭下稍稍歇下腳,又頂著一輪烈日繼續前行。在鄉下當了六年多鄉村教師,我似乎還像剛出校門那樣兩手空空。好不容易寫了本書出來,出書的錢是我向銀行貸的款。到了后來,還是我那剛進門不久的媳婦用自己的份子錢給我補的缺。我這樣一個寂寂無名的寫作者,出書不易,賣書更是千難萬難的事,擺不進書店,也吸引不了任何人的眼球。
于是,我可恥地打起了母校的主意。在經歷連續幾個晚上的失眠后,我終于在暑假里的一天,鼓起勇氣撥通了老校長的手機,剛聽他那里問出一個“喂”字,我便趕緊向他報告:“校長您好,我是2000年旅游一班的畢業生×××……”
話音一落,我便如鯁在喉,好似陷身于茫茫沙海,可以一口氣喝光一湖洱海。話聲磕磕絆絆,一顆心卻早已暴跳如雷,我趕緊找個凳子坐下來,同時用另一只手撫住心口,擔心它若是突一下子從嘴巴里蹦出來,我得趕緊把它接住。我不知是否把話說明白了,卻聽老校長在那邊開了口:“一個中專生,走出校門后沒有浪費光陰,當了幾年鄉村教師,還寫出一本書來,按說也是咱們學校的驕傲。雖然咱們經費的確有些困難,但幾十本書還是買得起的,放在圖書館,或是作為文學社的輔助讀物,也是對學弟學妹們的一種激勵啊!待新學年開學了,你給我們送五六十本來吧!”
就這樣,我終于在畢業多年后第一次回到了母校。當我卸下肩上的那重重一捆書,在圖書館大廳和老校長見上面,急著開會的他沒有像電話里那樣語重心長,給我簽了發票便匆匆離去。當我到財務室領到1500元的書款時,重負如釋的我忍不住又一次淚水如注。
那些可親可敬的師長令我時常感念并引以自豪,如今,老校長和許多任課教師都已退休,有的甚至已經故去,但我與母校、與老師們的情誼似乎沒有絲毫減少,相反還隨著時光的推移在不斷增長。
畢業25年來,我始終保存著在學校時萌生的文學夢想。我始終記得母校購買了我人生的第一本書,此后每當有新著出版,我都會在第一時間給母校送上,同時給敬愛的老師送上。而學校同樣對我大愛如初,在《洱海筆記》的兩次大型研討會上,如同散文詩朗誦一般給我至高的評價。當《洱海筆記》獲第十三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的消息傳來,學校為我編發了一則意義重大的微信公眾號推文……
留在記憶深處的溫暖,讓我始終覺得母校于我,就如汪國真詩里寫到的那樣:“我們也愛母親/卻和母親愛我們不一樣/我們的愛是溪流/母親的愛是大海。”作為一個被老師寵愛的學子,我相信不論自己走得多遠,都無法走出母校與恩師深愛的廣場。
(作者單位:云南省大理州教育體育局)
責任編輯:董曉娟
本文鏈接:TOP↑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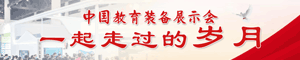






 首頁
首頁